苏联时期腐败概况
腐败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腐败现象在俄罗斯自古就有。在13世纪俄罗斯的编年史中就曾提到过受贿行为。伊凡三世对腐败行为第一次作出了法律上的限制。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腐败始终是地位不高的国家职员和官员不小的收入款项的来源。
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现象。1918年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侦讯委员会四名被指控犯有贿赂和恫吓罪的工作人员的案件,并判处他们六个月的监禁。列宁得知这一判决后坚决要求对案件进行重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判处其中三人监禁十年并剥夺自由。1918年5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受贿》的法令,这是苏维埃俄国第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法律文件。它规定,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或社会机关中任职的人,如被指控受贿,要受到剥夺自由不少于五年的处罚。在这个法令中把蓄意受贿或行贿等同于完全的犯罪。而且还规定了阶级的原则:如果行贿者属于有产阶级,力图要维护自己的特权,那么他要被判处“最重的、令人厌烦的强制劳动”,而所有的财产都要充公。这些都说明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有腐败现象存在。而且,在转向新经济政策后,腐败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
在新经济政策中止后,腐败现象并没有消除。随着斯大林在党内及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 立,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党政要员的特权。这首先表现为取消了党员的最高工资限额。苏维埃政权建立后,1920年曾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该决议为所有的共产党人,包括党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规定了统一的固定的工资等级。最高工资不应超过业务熟练的工人的工资。通过某种最高限度限制共产党人的收入在新经济政策初年还保留着。比如,1924年,共产党员工厂厂长的月工资是187.9卢布,而同样是工厂厂长——非党员厂长的工资是309.5卢布。报酬很高的共产党员应当按一定比例扣除一部分工资作为互助基金。1928年5月7日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规定,党员的最高工资一年为2700卢布。但这不是说党员不能挣多于这个总数的钱,比如拿到了稿费。但他应当把超过第一个27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20%作为党费上缴,从2700到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30%作为党费上缴,超过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40%作为党费上缴。从1932年起正式取消了党员工资最高限额,而开始实行时还要早一些。[2]其次就是二战后斯大林建议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发“党内津贴袋”。“党内津贴袋”是一个封口的信封袋,里面装着钱,按月发出。这种津贴相当于受益者正常工资的50%—100%。[3]
另外就是贪污贿赂现象蔓延。这主要发生在二战爆发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在1945—1953年间,因渎职罪、贪污受贿、侵吞财物、“精神生活堕落”、酗酒和流氓行为而失去党票的党员数量非常多。1945年7月1日到1947年7月1日,因上述原因被开除出党者占这一时期被开除党籍者总数的37.8%。而且,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要比其他地区领导人更经常地因“违犯苏联法律和歪曲党和政府的指示”而受到处罚。他们占因此而受罚的总数的31.1%和29.8%。因中饱私囊和在集体农庄中进行非法勒索而被追究责任的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占因此而受处罚者总数的35.4%。[4]以劳改营为例,当时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是劳动改造营中最为普遍的职务犯罪形式。比如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第12号劳改营管理局,犯罪分子编制虚拟的职务支付报表,甚至制造了虚拟的劳动队,其工资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获得了9万卢布的收入。这种行为在对劳动改造营进行检查时才被揭穿。再如,20世纪40年代末,内务部远东各区建设供应总局伊尔库茨克分局的主任会计把账目拿给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签字,在记入账目的总数前面留了不大的空地。这样,他随便在数字7000前面加了个4字,签了字的7000卢布的账目轻易地就变成了47000卢布的。会计通过这种手段成功地把340000卢布据为己有。1951年他被判处25年的监禁。据一份报告估算,1947年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第四局各个分队因盗窃、盗用公款和克扣发给囚犯的物品等造成的损失大约为15400000卢布,如果这个数字加上所谓的“糟蹋”(克扣发给囚犯的衣物),那么造成的损失与官方的资料一致,为20800000卢布。[5]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2750名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影子经济”(“第二经济”)萌生并发展。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执政阶层不用再提心吊胆地生活,用不着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有了安全感,这一时期的执政精英与老一代执政精英在价值观、消费观等方面都不同。他们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信仰,迷恋消费主义、物质世界。所有这些都为腐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腐败,就数量来看,1957年被定罪者为1800人,1970年为3000人,1980年为6000人。[6]
就搞腐败者的地位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来看,如果说在苏共二十大前,搞贪污贿赂的主要是中下层干部的话,那么二十大后,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很多贪污受贿都涉及到了国家高层人士,牵涉到了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等,而且涉案金额巨大。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检察院调查的将红鱼子和珍稀鱼类偷运出境的走私案,给国家带来几千万卢布的损失。犯罪网络的线索一直延伸到部级领导本人。[7]1982年破获的商业领域的最大舞弊案,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局长Н.П.特列古博夫被逮捕,受到审判,最后被枪毙了。之后又拘押了莫斯科商业总局25名重要工作人员和一些最大商店与食品店的经理,包括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所属食品店经理Б.С.特韦里季诺夫、“叶利谢耶夫斯基”食品店经理、卫国战争参加 者索科洛夫,还有“海洋”公司、“南方港”汽车商店和其他一些公司与商店的经理们。苏联商业部长А.И.斯特鲁耶夫被安排退休。据说该案的主要责任人特列古博夫与政治局委员维•瓦•格里申关系密切。[8]内务部领导层腐败案与领导内务部17年的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及其副手勃列日涅夫的女婿Ю.М.丘尔巴诺夫直接相关。仅丘尔巴诺夫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9]1983年10月31日,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夏•拉•拉希多夫因侵吞数十亿国家资金的乌兹别克棉花案件而自杀。接替他的伊•布•乌斯曼霍贾耶夫也被指控有受贿和舞弊行 为。勃列日涅夫的好友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被指控“粗暴地违反党的纪律”,并亲自出面保护高级领导中的受贿者。[10]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波及的范围很广,仅在调查晓洛科夫案件的过程中,内务部各机关被开除者就达10万人。[11]苏联的腐败在1980年代末和苏联解体时期随着全面控制的松动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开始达到了最大规模。
苏联时期腐败产生和盛行的原因
第一,对腐败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带有意识形态特点。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不使用“腐败”这个词,自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应存在腐败。按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腐败”一词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使用。以前使用的是“受贿”、“滥用职权”、“姑息”等术语。[12]在1962年3月29日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同受贿和偷窃人民财产行为作斗争》的密信中明确指出:受贿——这是“剥削社会的环境所孕育的社会现象”,十月革命消除了受贿的根本原因,而苏联的行政管理机关——党的、工会的以及国家机关的工作中的不足,首先是对劳动人民教育方面的不足成了腐败的原因。[13]1981年5月2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机关《关于1975—1980年加强同受贿行为斗争》的报告指出,1980年查出了6000多起受贿行为,比1975年多出了50%。讲到有组织的集团出现(比如,苏联渔业部以副部长为首的100多人);说到了各个共和国部长和副部长被判刑的事实、受贿及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与犯罪分子的勾结、检察院和法院中的受贿;通报了对处于领导岗位的党的工作人员(市委一级和区委一级)姑息受贿的处罚;认为短缺产品的划拨、设备和材料的分配、计划任务的更正和降低、重要职务的任命、暗中搞诡计等是主要犯罪要素;认为受贿的原因是在干部工作中存在严重疏漏,在审理公民的合法要求时的官僚主义和拖拉,没有很好地对待公民的控告和信件,粗暴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的和财政纪律,对受贿者的自由放任(其中包括法院的判决),没有很好地对待社会舆论。[14]以上这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腐败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反腐败的方式和力度。
第二,对腐败案件的处理存在双重标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很多腐败分子都有高层人物做后台,因此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处理受到了上层人物的干涉和庇护,而小腐败分子则成为替罪羊。比如,在商业领域最大的舞弊案件被破获后,当时的莫斯科民警机关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局局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间谍军官А.斯捷尔利戈夫回忆说:“无法无天的行为来源于党的机构……有的人因为40戈比的缺斤少两行为,就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一些大的投机者非法赚取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卢布,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证明说,调查商业部门中的舞弊行为的工作,引起了党的精英们的不满。调查行动是“受到控制的”[15]。1982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的舞弊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仍反对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将梅杜诺夫逮捕并交付审判的建议,而建议将其调到其他地方。[16]外贸部副部长苏什科夫因贿赂和舞弊被定罪,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盟总检察院向中央汇报了侦查的额外结果:部长帕托利切夫经常收取外国公司代表的黄金及其他贵金属制品和稀有的金币作为礼物。但事情却被压了下去。再如,1964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报告说,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为首的吉尔吉斯的整个党政领导,多年来是受一个分布广泛的黑市商人和地下社会的诈骗犯网雇佣的。已经证实,这些黑市商人和诈骗犯曾经建立了几十个秘密工厂、集体农庄和鸦片与大麻种植园。这些单位没有进行正式登记,也不向国家纳税,而其收入全部在从事这些犯罪活动的人和吉尔吉斯的统治者中间均分。实际上这纯系一个向该共和国的统治集团定期纳税、以便以一种在苏联罕见的规模自由从事犯罪活动的体系。一个共和国的统治集团被合盘揭露出来,这在苏联还是第一次,然而吉尔吉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其他党政领导成员均被撤换,但受到审判的却只有一名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地下社会的诈骗犯,其中有三人被行刑队处决。1969年阿塞拜疆共和国党政领导集团中三套机构的全部领导人(包括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委员阿洪多夫)都被发现由于委任党政官员、保护地下诈骗犯及其他原因而有组织地接受贿赂。但地 位最高的受贿者仍未受到惩罚。阿洪多夫被解除了第一书记的职务,但是数月后又被选为阿塞拜疆科学院的副院长。在格鲁吉亚,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和第二书记丘尔金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受贿案被内务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揭露出来。但莫斯科同样让所有的高级受贿者都免受惩处。姆日阿瓦纳泽甚至没有被开除党籍,反而得到了一种大约比付给苏联普通人最高养老金多四倍的特别养老金。丘尔金虽被开除党籍,但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卡利宁州消费合作社的头头。[17]罗伊•麦 德维杰夫在自己写的安德罗波夫传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情况,“我在1991年初有机会翻阅了科列瓦托夫•布里亚采(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交往甚密——引者注)和一些商人的大量案卷。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审讯记录和判决书,都列有无数侵吞国家财产和贪污受贿的材料以及没收珍宝的长长的单子。但是在这些附有数百件各种证明文件的案卷里根本没有提到受审人同加林娜•勃列日涅娃、晓洛科夫家族、格里申家族或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关系。”[18]这些说明了很多大腐败分子还是受到了保护。按一位研究列宁格勒腐败案的研究者所说的:“禁止护法机关对担任干部名册中的职务的人 进行有效的整治。追究党员的刑事责任要征得区委的同意,如果是负责任的工作人员,那么只有市委或州委第一书记才能批准。”国家对高官的袒护,对反腐败斗争的控制,非但不利于反腐败的进行,反而助长了高层的腐败。
第三,腐败的盛行与“影子经济”的出现和市场经济因素向计划经济的渗入密切相关。非法的“影子经济”要存在和发展,就需要有国家企业或集体农庄做掩护,需要获得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紧缺的原材料、设备等。这些东西在当时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就只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这就为贪污腐败创造了条件。正如一位研究“影子经济”的作者所说的,非法贸易和生产导致大量贿赂行为。如送贿给审计员、检查员、计划部门的物资分配人员、“第一经济”里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为了要他们分给一些原料或要他们为地下企业制造一些东西)、经济警察(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警察)和普通警察、各种各样的党政官僚头头。
第四,缺少独立的监督机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官僚主义就在其内部复活并迅速蔓延。
党员的官僚主义习气严重,政府机构庞大,办事效率低下。作为监督政府机关和其他行政部门工作的工农检查院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方面表现不 佳,而且本身也表现出了浓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另外,内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化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党内的民主风气,政治局逐渐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决策机构,作为党的领导机构的中央委员会徒具虚名,威信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列宁开始了在党内建立一种权力制约机制的探索。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党的监察工作。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中央委员会约束,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当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间在处理的问题上有分歧时,则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处理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解决。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决定正式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察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并享有发言权;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消。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或代表大会解决;监察委员会可以利用本级党委员会的机构,并有权给所有的党员和党组织委托任务。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违纪 行为进行处理时,应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
如有2/3的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执行。1922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使监察委员会的机构编制进一步具体化。
1923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二大根据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书面建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关,对党政机关和干部进行纪律检查和监督。十二大使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的三个固定代表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审查文件;中央监委有权协助党和国家挑选领导干部或对其撤职查办;有权监督党和国家决议的执行情况,监察委员有权通过其主席团向中央全会、政治局和组织局提出议案。
列宁努力建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的独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要防止官僚主义问题和保证党内高层的团结,防止列宁晚年最为担心的足以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党内分裂。加强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把政治局置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最终达到限制总书记的无上权力和加强工农检查院的目的。用列宁的话说:“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 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19]
但在列宁去世后,苏共的监察机制逐渐失去了对政治局的监督、制约功能,监察委员会也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列宁设想的建立一个只对党代表大会负责的独立的监察系统的构想逐渐遭到了破坏。1934年的联共(布)十七大使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撤消工农检查院,将其对国家机关的监察工作并入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将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其职权主要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不再对中央起制约和约束作用。同时代表大会还规定“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这实际上也就使得曾与中央委员会处于平行地位的监委成了书记处的附属机构。到1939年党的十八大,又将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改为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使之完全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彻底丧失了独立性,这就使党中央的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腐败。
【注释略】
网络编辑:客卿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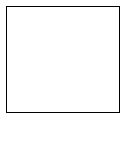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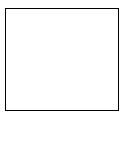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